郭进拴|登锅底山(3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:【郭进拴原创】登锅底山 为了却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的夙愿,在一个金风送爽的九月天,我和文友相约登游了位于新城区东部的锅底山。 我们一【郭进拴原创】登锅底山
为了却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的夙愿,在一个金风送爽的九月天,我和文友相约登游了位于新城区东部的锅底山。
我们一大早就从新城区湖光花园出发,经市政大厦前的文化公园、生态公园、过森林半岛,来到了锅底山下。放眼望去,锅底山还真像一个倒扣着的大锅,这其中有什么原委呢?
带着疑问,我们开始登山。正行间,忽见一岭拔地而起,纵插霄汉,体青脊黑,莽莽苍苍,蜿蜒盘旋,真好似苍龙腾空,鬼斧神工,惊险奇妙。一旁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壑,势陡如削,崖下林涛呼啸,凉风袭人。

穿过一片密林,只见绿油油的桃树,在山风吹拂下,悠扬多姿,斑斓的各色山花点缀其间,更添几分诗情画意。林中的流泉飞瀑,水色清清,水花晶莹,有的像绿竹朱岩间的根根银带,有的似从天宇飘然洒下的匹匹绸绢。间或有轻纱似的薄雾萦绕其间,雾中传出淙淙溪水的弹琴声,白胸翡翠和红嘴蓝鹊的欢叫声,松鸭和太平鸟轻快悦耳的歌唱声,汇成了一曲优美动听的大合唱。
锅底山上有一眼泉,以清、静、甜、醇闻名。那泉水清流脉脉,如线似缕,碧波闪闪,如锦似缎,日日夜夜,叮叮咚咚,就像一位九天仙女躲在幽处用纤纤细手在不知疲倦地拨动着琴弦。我捧了一掬泉水,一饮而尽,只觉那泉水甘甜可口,清凉透骨,颇有醇酒甘露之美。据说这眼泉叫玉泉,与山下湖滨生态公园的一眼井是相通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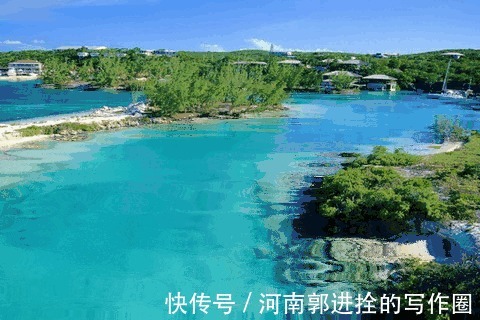
当我们登上锅底山顶时,东方地平线由乳白渐泛赭黄,金辉四射。刹时,红日喷薄欲出,就像一颗巨大的气球,冉冉上升。红日驱赶着黑暗,撒播着黎明,仿佛风卷残云,直射中天。于是,群星急忙隐去,天空明朗如洗。山峦、树林、河流、湖泊、田野……全部都披上了一身金衣。此刻,百鸟齐鸣,山呼谷应,满山野花,娇艳似火。霎时间,晴空万里,大地如画,山上的树林,也由一片黑森森的颜色,变得碧绿鲜嫩了。
我们站在锅底山顶,望着显得很低的天幕,似乎一伸手就可以从云屏中扯出几块云纱。我们在建在锅底山顶的移动基站旁席地而坐,听一位“鹰城通”讲起了锅底山的来历:据说很久很久以前,这山上住着一个老道人,终日合掌诵经,修身养性,自称黄花道人。黄花老道有三个徒弟。大徒弟普静,瘦小精明,能说会道。他是庙里的管家,经常到山下去求斋化缘。二徒弟普海,牛高马大,有一身力气,每天到山上去砍柴。三徒弟普生,心地善良,憨厚老实,烧火做饭、打扫庙堂,摆供上香和侍奉师父等,都是他的事。
三个徒弟住一间屋里,每天天不亮,普静就说:“该起床了!”自己却不动。普海也说了一句:“还有柴呢!”然后继续睡觉。只有普生早早起来提水做饭,扫庙上香,然后伺候师父起床、师兄吃饭。等到他吃饭时,只剩下了一点点稀汤寡水。

三个徒弟跟黄花道人学了三年,普静和普海觉得什么也没学到,他俩就经常嘀咕说:“都说师父是个仙人,也不见得有什么真本领,这样下去,啥时才能成仙呢?”只有普生一声不响,每天默默地做他该做的事。后来普静和普海见师父还不传给他们仙术,便经常躲到山下去玩,很少去化缘和砍柴了。普生见存粮越来越少,就自己挖些野菜充饥,把米饭分给师父和师兄吃。尽管这样,到底还是断炊了。这天早上,黄花道人叫来了三个徒弟,问他们为啥没有准备早斋。三个徒弟面面相觑。普生给师父施礼说:“不是徒儿偷懒不做,而是没有粮食了。师父要怪罪,应怪我平时不知节省,与两位师兄无关。”说着,掉下两串泪珠来。
黄花道人转问普静:“徒儿,你化的粮食呢?”普静也施礼说:“不是徒儿偷懒,是山下百姓太穷,我跑了九九八十一个村庄,也没有一户人家肯施舍。”黄花道人又问普海:“徒儿,你砍的柴呢?”普海施礼说:“不是徒儿偷懒,是山上的树木都叫徒儿砍光了。”
黄花道人听罢,有气无力地说道:“饿煞贫道也!”说完,昏倒在禅座上。普生上前抱住师父,不住地哭叫着。普静和普海相视一笑。普海低声说:“一顿饭没吃,就饿得要死,肯定不会有什么仙术。”普静点了点头。
